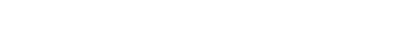刘宗贤:当代东方儒学复兴的启示
作者:刘宗贤时间:2003-03-25当代东方儒学复兴的启示
论文提要
刘宗贤 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所
一
东方儒学成为东、西方共同瞩目的研究对象是在当代的事,然而东方儒学作为东方学中的一个学科概念的成立,却是有着深厚的全球文化背景,和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的。
首先,就东方的概念看。东方,是以悠久的文化传统著称于世的,然而东方的概念却带有相对性、多歧义性和不确定性。其内涵既包括地理的,又包括民族的和文化的,同时,也带有某种政治的含义。
作为地理概念的东方现在一般指亚洲和非洲中部、北部地区,也往往泛指东半球。然而东方既是相对西方而言,历史上处于东、西方的国家和民族便会由于全球知识的缺乏和主观眼界的限制,而对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解释。在中国古代,所谓东方和西方都是以自身为中心来确定的。而在西方中世纪时代,地中海曾被看作世界的中心,由这一中心来确定东、西的概念。中世纪以后,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中心转到西北欧,世界的范围也扩大到南美洲和北美洲,这种地理和文明范围的扩大,也导致东方概念的变化。
东方概念又受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16—17世纪,西方向东方扩张,按离西欧的远近来划分东方世界的层次,依次分为近东(地中海到波斯湾)、中东(波斯湾到东南亚)、远东(太平洋地区—指东亚和东南亚国家)。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以来,东方掀起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扩张的民族主义运动,形成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因而东方的概念又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至今,人们称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为西方世界,称社会主义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为东方世界,表明了东方概念向政治,及经济方面的延伸。
东方的概念如此,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东方学研究应是一门历史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学问。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在他的著作《东方学》中所说的:“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①以往,西方对“东方学”的研究难免带有对东方国家民族的歧视和偏见,而东方民族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自信的发展过程。
二
儒学作为东方学的研究范畴无疑是从文化现象和历史文化传统方面说的。
就民族和文化的意义上说,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经历和创造着独特的东方文明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像四座灯塔屹立在北非、西亚、南亚和东亚,它们标志着古代东方文化的辉煌。今天,在亚洲和北非的土地上,仍生活着1000多个民族,约占世界民族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在人口数量、种族特征、语言属系、宗教信仰,或是在社会发展、经济活动、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上,都是千差万别的。②就历史文化传统方面说,英国汤因比等西方历史学家,把过去人类文化或文明分成许多独立的个体,演成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文化圈的说法。如果把世界上四大文化圈分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话,那么西方文化体系指从希腊、罗马,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东方文化体系则包括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等三大文化圈。中国文化圈的中国、日本、朝鲜(北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都受到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很深的影响。因而中国文化圈也叫儒学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所谓汉文化圈,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适用于四邻的汉字。”③而汉字,以其独特的个性迥异于西方拼音文字。
综上所述,无论从东、西文化的差别,东方文化的不同类型,以及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圈内各国所受到儒学的影响来讲,儒学都应该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以往儒学在世界范围内是没有被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体系研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存在着鸿沟,这种鸿沟曾被认为是无法逾越的。近现代,欧洲(英、法、德等)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往往更多地集中于汉学的专业化领域;另一方面,则由于儒学在它的原发地——中国所经历的特殊遭遇。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儒学在中国屡遭挑判,日益衰败沉沦,被当作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封建保守主义的同义语,直至在“文革”中被彻底打倒。因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儒学及儒学研究都没有,也不可能进入中西交流、东西交流,或东方文化研究的领域内。
儒学作为东方的一门古老的学术文化,其成为当代的话题,并引起东西方人士的共同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70年代东亚经济腾飞,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它一些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推进,显示出一种有别于欧洲的“集团主义人文类型”④的现代化模式。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的斐然成绩,不仅令西方经济界瞠目,而且使得许多西方人士意识到:亚洲今天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革背后,有一个传承数千年的历史背景。不少人惊呼,东方的传统文化已经觉醒,并且在建设新生活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以及西方学界才认真地加紧了对东方及东方传统的研究。继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的比较社会学研究之后,东西方关于儒学的许多新提法,如亚洲价值、亚洲传统、亚洲式的个人与家庭价值观,以及“新儒教文化”、“儒教资本主义”、“儒教文化圈”等纷纷出台。东亚各国也意识到需要重新对东亚进行再认识,因而更加重视起对自身传统的研究和评价。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儒学也不再只是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界和政府都越来越关心传统文化的作用及儒学的价值问题。
三
以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东方儒学的复兴。之所以用复兴而不用“复苏”,是因为今日的儒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古老的学术文化的层面,它经历了近代以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合,经历了东亚一些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以及文化的觉醒而得到新生;在内容上,它包容了东方以及东方学在地理、政治、经济,乃至民族、文化、文明、社会发展、经济活动等多方面的内涵。
那么,东方儒学的复兴,给我们作为儒学原发地的中国,对于儒学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及儒学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启示,又提出了什么问题呢?简略言之:
(一)儒学是一种世界性精神文化资源。
(二)儒学研究应该走出中国,走出东方。
(三)儒学的生命力在于普及和传播。
注释:
①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6—7页。
②李毅夫:《东方民族与文化》,见《东西文化议论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328页。
③[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④[日]小林多加士:《东亚:转型现代化的新范式》,罗荣渠等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