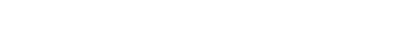李亚彬:天人观视野下的孟荀人性论之争
作者:wind时间:2004-11-22天人观视野下的孟荀人性论之争
李亚彬
(《光明日报》理论部,北京100062)
[摘要] 孟子、荀子间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源自天人观上的分歧。孟子之天人合一乃个体的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荀子之天人相分为群体的人与自然之天的分离。孟子以心善言性善,认为性在心中;荀子以欲望为人性,认为性在身。在孟子,天人因道德而合一;在荀子,天人因道德而相分。
[关键词] 性善; 性恶;天人合一; 天人相分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4)05-0073-06
人性论是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孟子、荀子虽相去百余年,但二子性善论与性恶论跨越时空的对话,穿透历史的交锋,不断撞击出绚丽耀眼的火花。这个争论是儒学内部最重要的争论之一,它深刻地影响着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一定的人性论主张是道德哲学建构的必要前提。二子所争论的焦点在于何为人性,以及人性是善还是恶。孟子以人的道德属性为人性,荀子则认为人性是人的生理欲望。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因为人性中固有善的萌芽与动机;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因为人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无限的欲望中潜伏着社会冲突,即包含着恶的结果。在争论过程中,孟子、荀子分别以性善论和性恶论为逻辑前提建构了以仁为核心的仁学和以礼为核心的礼学两个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但人性究竟来源于何处?道德的最终根据又在哪里,答案在人自身无法找到,而要追溯到天那里,要在天人关系中寻找。因为天人观是中国人基本的世界观,无论是人性论还是道德哲学,都是以一定的天人观为基础的。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孟子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论,荀子则明确主张天人相分。这两种天人观相互对待,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天人观。在天人观的理论框架内,孟子、荀子分别解决了人性的来源及道德的最终根据问题。可以说,孟子、荀子的分歧源自天人观上的分歧。
一
确立何为人,亦即明确人具有怎样的规定性,是建构关于人的理论的前提,也是人性论和道德哲学的前提。人与道德是同一的,这是儒学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人与道德应该同一,但现实中却是不同一的,这是儒学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儒学的使命在于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即实现善——合道德的人生、合道德的社会。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不同的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同的。这是人们对“人”产生不同认识的根本原因。孔子在初创儒学时,打破了周以来人与人的诸差别,重新确立了“人”的观念。
一是打破了国人与庶人(野人)、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周初平定武庚之乱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分封制。由周朝的皇亲国戚率领周人进驻被征服地区,建立城堡,称为“国”。周人居住在城堡中,称为“国人”。被征服民族被赶到城堡外的野地生活,称为“野人”,因他们地位低于国人,且人数众多,又称“庶人”。庶人(野人)不仅不能像国人那样参与、议论国家政治,而且被剥夺了当兵打仗的权力。他们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不得迁移,世代为其所隶属的贵族劳作。周统治者在推行分封制的同时,为确保权力掌握在最亲近的人手中,又推行以“亲亲”为原则的宗法世袭制,将国人中的非贵族阶层完全排斥于统治集团之外。以是否拥有政治权力为标准,国人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大阶层。君子包括王族、公族、大夫家族、上层士,他们是周的贵族;小人则是国人中没有特权的人,他们虽为统治民族,但实际上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生活上自食其力,战时还必须当兵打仗。在宗法世袭制度下,统治者只能从君子阶层产生,小人从政几乎不可能。西周末年,随着国人数量的增加,国人作为统治民族的身份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包括远房庶出子孙在内的贵族成为没有继承权的国人,因无法占有采邑或近郊耕地,不得不移居到野地上开荒种植而沦为庶人。还有一些古老的贵族世家,由于与国君关系逐渐疏远也成为庶人,有的甚至沦为奴隶。在周代,奴隶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只是奴隶主贵族的私有财产,其地位甚至不如牲畜。而孔子却破天荒把他们当做人来看待。《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显然,孔子不是从把奴隶与牛马同视为财物的奴隶主贵族立场上去提问,而是从人道角度提问的。在他看来,奴隶的生命比牲畜重要得多,因为他们与其主人一样也是人。孔子还把对庶民的“不教而杀”列为“四恶”之首,他严厉谴责“作俑者”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孔子斥责第一个制造木偶、土偶用来殉葬的人应该断子绝孙灭绝后代,因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用象征活人的人形木偶、土偶来殉葬尚不可,又怎能使百姓活活俄死呢?孔子还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原则,主张应对所有的人进行教育,而不应有贵贱、贫富、地域的差别。总之,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把庶人(野人)、小人看成人。
二是打破了华夷之别。在周四邻地区有许多少数民族部落,即使在中原地区也有一些非华夏族的部落。他们历来被蔑称为“夷”、“狄”、“蛮”、“戎”等。春秋以来,它们逐渐与华夏族融合。《论语·子路》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子欲居九夷。或曰: ‘陋,如之何? ’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远者”指封域以外的不同血缘或不同种族的人。孔子主张对他们采取招徕、团结的态度。即使“不服”,也要“修文德”去影响他们。在他看来,“仁”德既适用于华夏,也适用于“夷狄”,这与“以族类辨物”的血缘宗法等级观点是对立的。陋是出于小人的鄙狭之心,与九夷并无关系。孔子说:“夷夏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意即“夷狄”不如中原文明。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就是说,环境决定人。这恰如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孔子认为,夷人生活在文明地方,也会变为文明人。因而,华夷之别并非不可改变。
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差别。孔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别,代之以君子、小人之别。在孔子看来,君子与小人之间最本质的差别是道德水准的高下。他常以君子、小人对举,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同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等等。这样,君子、小人原初意义上的差别已基本消失。小人完全可以通过受教育,加强自身修养成为君子,而在过去的意义上,小人与君子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此基础上,孔子重新确立了“人”的概念,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差别,如智愚、文野、华夷等,但本质上是平等的。这个平等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人生而平等”,而是“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别都不能成为人追求道德完善的障碍。这一观念的确立为整个儒家学说的确立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观念,才能打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的传统,使道德成为对上至国君、大夫,下至庶人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这对于为生逢乱世、身处动荡之中、价值失落的人们重新确立生活的目标,为他们的生活赋予意义,唤起他们生活的勇气,是极其重要的。孔子创立儒学,就是要用道德来整饬社会,重塑人生。其开天辟地的意义用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语来评价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荀子分别提出了“人禽之辨”,明确主张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道德,而禽兽没有道德。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他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非常小,君子与一般人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道德的萌芽。如果人只知道吃得饱、穿得暖、住得舒适,而没有得到教化,那就几乎成了禽兽。荀子也提出了一个与孟子极为相似的命题:“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荀子认为,人之为人在于有上下、贵贱、长幼、亲疏的等级区分,在于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在于有礼,亦即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一定的道德规范。显然,在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具有道德这一点上,荀子与孟子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有道德即为人,无道德即为禽兽。只有人才有道德,道德只是人的道德,它的惟一属性是属人的,人与道德是完全同一的。所不同的是,这个同一在孟子为直接的同一,在荀子则为间接的同一。因为,孟子之道德的本质为道德意识,荀子之道德的本质则是道德规范。
道德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外在的道德规范,一种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意识。人是社会的人,个人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总是把一定的道德规范内化到每个人的心灵中,成为他的内心信念、价值尺度和善恶标准,亦即道德意识。需要说明的是,在类、个体的人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道德规范的形成及道德意识的产生交错在一起,无法分开。所以,这种区分只是在思维中存在。
孟子所谓人性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他以人心中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为人性。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四心”是人之为人的标准,又是仁、义、礼、智“四德”的萌芽、端倪:“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四端”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规定性,它“非由外铄,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即天生而有之,就如同天生而有四肢一样。孟子为了说的方便,甚至还直接说“四心”就是“四德”。人的道德由此而生。如果将“四心”比喻成树木种子的话,那么“四德”就是大树,道德形成就是由“四心”发芽、生长的过程。这一切都是从心开始,在心中完成的。显然,“四心”(“四端”)、“四德”的本质是心中的道德意识。
荀子反对孟子的道德先验论,持“圣人制礼义”的观点。他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王霸》)在荀子看来,眼、耳、口、鼻、心的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性。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一定的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他就会不断去追求。如果这种追求没有一定的限度和界限,人与人之间就不得不互相争斗。争斗会导致社会混乱,使社会穷困。于是,“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王制》)“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古代圣王制定了礼义,对人群进行了等级名分的划分,使不同的人各得其宜,从而避免了因互相争斗导致的社会解体。在荀子看来,道德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不是先验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先验的道德原则或伦理标准,一切道德原则、伦理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可见,荀子的礼的本质是道德规范。
人具有身心即生理和心理两个部分。孟子以人的道德属性为人性,认为性在心,注重人的心理情感,得出人一心向善的结论;荀子则认为人性是人的生理欲望,以身为性,偏执于人的生理欲望,得出人一身向恶的结论。孟子着眼于个体的人,认为人性本善,他所谓道德乃心中固有的道德意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道德意识在人自身之内;荀子着眼于群体的人,认为人性本恶,他所谓道德为圣人制造的外在的道德规范。因而,人与道德的同一在孟子,为(个体的)人与道德(意识)直接同一;在荀子,为(群体的)人与道德(规范)间接同一。但孟子、荀子何以对人性及其性质做出各自的规定,他们之道德(意识、规范)的根据又何在呢?答案在天。
二
孟子之天主要为义理之天,荀子之天主要为自然之天。冯友兰说:“孟子言义理之天,以性为天之部分,此孟子言性善之形上学的根据也。荀子所言之天,是自然之天,其中并无道德原理,与孟子异。”[1]
孟子义理之天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主宰之天。《孟子·万章上》记载了孟子与其徒万章关于天为人事主宰的一段对话。在孟子看来,“舜有天下”是“天与之”的,而非“尧以天下与舜”。同样,禹、启为天子也是天的安排。前任天子只能向天推荐继承者,至于天是否采纳其推荐,则并不一定。舜继尧、禹继舜,天均采纳了前任的推荐,禹之后,天并没有选择禹推荐的益,而是选择了禹的儿子启做天子。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由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转变。孟子却把这一切看作天的安排。在他看来,对于谁来做天子,天自有其安排。这个安排的根据何在呢?在于继任者的表现,看他是否有德并得到百姓的拥戴。舜、禹不仅能够长期辅佐前任治理天下,而且得到百姓的赞同,所以,天选择他们做天子;而益辅佐禹治理天下、对百姓的恩惠时间不长,所以,天未选择他做天子;因启贤德,天选择了他作天子。孟子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解释来说明天是人事的主宰,人的社会是由天来安排的。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把天人格化。
第二,命运之天。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梏桎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尽心上》)同孔子一样,孟子论天,总是和命相联系,命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正是天主宰人事的结果和表现。没有人叫他们这样做,却这样做了,便是天;没有人叫他来,却来了,便是命。在孟子看来,没有什么不是命定的,顺理而行,便会得到正命。所以,知命的人不会站在快要倒塌的墙下面。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正命。
第三,义理之天。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仁义忠信等道德品质及永不疲倦地追求善,是天之最高贵者,公卿大夫是人之最高贵者。诚是天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在孟子看来,天本身就有道德,甚至它就是道德本身。
天的这三层含义层层递进。应当说,第一种含义是最基本的,第三种含义更为根本,因为只有这层含义才可能实现人道与天道的贯通。人之有“四端”,人性之所以善,正因为人性乃“天之所予我者”,是人之得于天者。无论哪种含义的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为,即“莫之为而为”,天自己决定自己,它只是施动者,而不是受动者。
与孟子不同,荀子吸收了道家思想,消解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他之所谓天完全是自然之天。
第一,天“自然”。荀子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天一方面指的是日月星辰、阴阳四季及风雨等自然现象,另一方面,它还自然而然,自我规定,是造物之主,万物皆从它来。荀子进一步剔除了天主宰、命运的含义。他说:“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怪异的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如果君主贤明、政治稳定,几种怪异现象同时出现,也不会产生危害;如果君主昏庸、政治险恶,怪异现象都不出现,也不会有好处。
第二,天有其道。也就是说,天有自己运行的规则和规律。这个规则和规律是独立于人的。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天有天道,人有人道。这是两种不同的规则和规律,且互不干预。
三
孟子、荀子对人及天的规定已经蕴含了他们在天人关系上的分歧。孟子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荀子则主张天人相分。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人虽各有其道,但人道来自于天道,人道服从于天道。张岱年认为:“……所谓天人合一,有二意义:一天人相通,二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观念,发端于孟子……认为天之根本性德,即含于人之心性之中;天道与人道,实一以贯之。宇宙本根,乃人伦道德之根源;人伦道德,乃宇宙本根之流行发现。本根有道德的意义,而道德亦有宇宙的意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即在人之心性与天相通。人是禀受天之性德以为其根本德性的。”[2]这段话一语道破了天人关系中蕴含着人性的来源及道德的根据。在孟子那里,天有道德,它又按照自己的面目和要求塑造了人:赋予人以人的规定性——人性,同时把道德植入人的心中,成为人特有的道德意识,从而把人和禽兽区别来。这样看来,人为天所生,人与天本来就浑然一体。在这个过程中,心的作用特别重要,它是道德的承载者。孟子提出了“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的命题,认为“心”是思维器官,具有“天之所与我”的思维能力。心具有天赋的认识能力,这个天赋的能力也就是“不虑而知之良能”、“不学而能之良知”(《孟子·尽心上》)。这样,“心”便能够接受天所赋予的道德意识。于是,天把“四心”即四种最基本的道德意识植入人心中,从而实现了人与天的合一。可以说,人是依靠天来规定的,人的根据在天,道德的最终根据也在天。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因为人心与天是相通的,所以,只要“尽心”,就可“知性”、“知天”;只要“存心”、“养性”,就可“事天”。总之,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在他那里,性在心中,心性为一。他以心中的道德意识为人性,而道德意识又是天赋的,所以人性来源于天,道德的根据亦在于天。这样,孟子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解决了人性的来源及道德的最终根据问题。
所谓天人相分是指天人各行其道,天道并不干预人道。传统观点认为,在天人关系上,荀子持天人相分的观点。这固然不错,但如果仅仅这样认为,尚不能领略荀子思想的真谛。其实,天人相分是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这个合一不同于孟子。其本意是人为天所生,是天的一部分。人与天原本是合在一起的。无合则无分,无分则人无以为人。
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无论是作为类还是作为个体的人,其所谓“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都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仅具有自然属性,但这自然属性不同于动物的自然属性,因为其中包含着社会属性的种子、胚芽,它只为人之为人提供了可能性,至于能否成为真正的人还在于能否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获得社会属性,因为只有社会属性才是人与动物相区别、人之为人的特质。在这个阶段,人的社会属性尚未确立,只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自然属性之中。第二阶段,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社会不断地把各种社会关系赋予每个个体的人,潜存于自然属性中的社会属性逐渐确立起来,成为人之为人的特质。只有在这个阶段,人才真正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成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的真正的人。[3]同样,荀子之“人”的发展实上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禽不分,人完全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合一,并无任何特别之处。荀子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万物为自然所生养。万物是道的一部分,具体的物又是万物的一部分。这个道即是自然运行的总规律。人作为一具体之物,同样是万物乃至道的一部分,同样为自然所生养。在这一点上,人与万物并无区别。荀子对人性“生之所以然谓之性”的规定也是以这个阶段的人为标准的。在他看来,所谓人性是自然生成的人的本能,是“不可学”、“不可事”的生理欲望,即“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性恶》),“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荀子·王霸》)这些欲望是天生的,是“生而有”、“无待而然”的,是“本始材朴”(《荀子·礼论》)。总之,荀子以欲望为人性,性在身。而欲望又禀受于天,所以人性出于天,是谓“性者,天之就也”(《荀子·正名》)。天在规定人性的同时,也将一定的认识能力赋予人。荀子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荀子认为,人有能知之才,物有可知之理。有了认识能力,人就能够学习礼义,“化性起伪”,改变人性,积善成德。
第二阶段,人从自然之中脱颖而出,超越众物,成为自然的对待之物,成为“自然之尤”。荀子说:“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荀子把万物由低级到高级分为四个层次:有气无生的水火,有生无知的草木,有知无义的禽兽,有气、有生、有知、有义的人。这个划分从无生命的水火等物质到有生命而无知觉的植物,到有生命、有知觉动物,再到有生命、有知觉、有道德的作为高级动物的人,是符合自然界的进化规律的。人虽然与水火、草木、禽兽同为自然所生,但却高于它们,根本原因在于人有道德。他进一步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在荀子看来,人有了道德就能够合群,即组成社会。这也是人能够高于水火、草木,使禽兽为人所用,并从自然界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荀子所强调的“明于天人之分”,实是要人区别开第二阶段的人与自然的区别。道德本身是人在自然属性基础上获得的社会属性,它使自然的人成为社会的人,亦即成为真正的人。只有到了第二阶段,人才把自身与天分离开来。所以,荀子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要有所作为,就要“制天命而用之”(同上),即掌握并利用自然运行的规则、规律,从而为人谋利益。在此基础上,达到与天的和谐,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同上)在他看来,天有时令变化,地有资源,人则有治理自然、社会的努力。这就叫做能与天地配合。如果人一心向往与天地争职能,那就是糊涂了。可见,人原本为天所生,自从有了道德,就与天分开了,成了与天相对立的异己。但人的生存与发展不但不能脱离自然,反而要与自然相配合,相和谐。于是,荀子把天道与人道贯通起来,在天人相分的框架下,为道德确立了最终的根据。
梁启超说:“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综观经传所述,以为天者,生人生物,万有之本原也;天者有全权有活力,临察下土者也;天者有自然之法则,以为人事之规范,道德之基本也。故人之于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为基焉。”[4]言天是为了言人。探讨天人关系,是为了从中寻找人伦道德的根据。孟子之天人合一乃个体的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荀子之天人相分为群体的人与自然之天的分离。无论在孟子还是在荀子,人性皆出于天。在孟子,天人因道德而合一;在荀子,天人因道德而相分。孟子、荀子从不同的天人观出发,对人性及其性质作了不同的规定,并为道德确立了根据。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1.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8.
[3]李亚彬.孟荀人性论比较研究.哲学研究.[J].,1994,(8)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
[收稿日期] 2004-04-06
[作者简介] 李亚彬(1969-),河北保定人,哲学博士,《光明日报》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
(责任编辑 李 理)
The Conflict between Mencius and Xunzi about Human Nature in the Visual of Heaven and Man Relation
LI Ya-bin
(Department of Theoretics ,Guangming Daily , Beijing 100062)
Abstract:The conflict between Mencius’ doctrine of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and Xunzi s’ that of evil originates from the difference on the point about heaven and man relation. Mencius’doctrine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means the unity of moral heaven and singal man.Heaven has moral ,also it makes man according its own face and demand.It endows with man character as his human nature,while put moral consciousness into his heart .So man separates himself from animal. Xunzi s’ of the distinctive of heaven and man means the distinctive of natural heaven and man as colony,it has two periods :in the first period, man is unity with heaven as a part of it,while in the second, man separates from heaven because of getting moral dicipline ,and becoming the opposite to heaven. Xunzi s’ understanding the doctrine function of heaven and man refers to the second period. Human nature is endowed from heaven. Mencius’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means the goodness of heart,he thinks human nature is in heart. Xunzi regards psychological desire as human nature, he thinks human nature is in man’s body. According to Mencius, the heaven and man are unity because of moral consciousness;in the viewpoint of Xunzi, the heaven and man are distinctive because of rules of morality.
Key Words: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the evil of human nature;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the distinctive of heaven and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