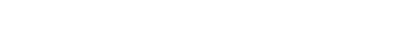向世陵:从以孝为核心看家庭伦理与社会国家伦理的一体性
作者:向世陵时间:2007-05-25
[内容提要]“孝”是传统伦理的核心。“孝”之意义不仅在维系家庭,更在于安定社会国家,二者的统一是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五伦”作为传统伦理的主干,虽然有平行(夫妇)和上下(父子)关系的不同类型,但随着孝道的进一步贯彻,主要已体现为父子有亲而夫妻不爱。淡化夫妇而强化父子所引出的,是社会国家迫切需要的维持上下尊卑的“忠”的原则。“孝”与事功和事业相关,忠孝不二是为至善。传统孝道的负面的意义应当予以正视,变上下尊卑为平等相爱。
[关键词] 孝 五伦 夫妇 父子 爱
———————————————————————————————————————
家庭伦理与社会国家伦理的一体性,是中国传统伦理观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之所以可能,既在于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的现实,亦在于以维护这一现实为己任的儒家学术的自觉。在儒家,家庭伦理无疑是全部伦理关系的起点,一切伦理原则和规范都是植根于家庭血缘亲情的基础上的。但是,“家”的概念在中国社会却有它的特殊性,其本义——大夫的采邑原是与“国”不可分的。一国分数家,“大家”共一国,这就必然影响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伦理,并最终决定了家庭伦理和社会国家伦理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和互通性。从此意义说,完全局限于家庭内部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虽然也有自身的价值,但在传统社会却是不占主导地位的。
(一)伦理与五伦
“伦理”一词,《礼记·乐记》是将它与音乐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曰:“伦,犹类也;理,分也。”如此的类、分,本是指人高于禽兽、君子区别于众庶而识音知乐的品性,但因其“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同上)的进一步发明,就使伦理与以礼为代表的社会政治需要密切联系了起来。那么,以类别或分类来解释的伦理,也就自然地过渡到人在社会中的定位和等级的差别。不过,这种人际的类别区分并不能直接导出不同等级的人们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需要哪些规范才能最为简明扼要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划分得更为合理并促使人们遵守,是战国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思想家才明确揭示出来的。
按照孟子的概括,伦理,或者说伦常,是圣人为了解决人民“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以致近于禽兽的迫切需要而制定出来的:“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是即所谓“五伦”。
从如此的“五伦”可以看出,严格意义的家庭伦理只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两项,属于社会伦理一方的也是两项——君臣(有义)和朋友(有信),家庭与社会兼有的一项——长幼(有序)。家庭的这两项到了后来孔颖达疏解《古文尚书·泰誓下》的“狎侮五常”时,已推演成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项,即在形式上五伦已全归于家庭伦常。然而,商王这里虽然有家庭的因素,可实质上仍是国家政治关系,所以紧接着才有“自绝于天,结怨于民”的谴责。这就有助于说明,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核心不在自身,而在于它必然与之 相连的 君臣关系、社会政治关系亦即礼制上。
(二)夫妇与父子
《周易·序卦》在解释咸(感)卦交感的卦义时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 后有 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如此的推论,一般来说是符合人类社会的起源和人伦礼义的形成过程的。它说明最根本意义上的家庭伦理仍限于夫妇、父子这两项,而这两项又必然过渡到君臣关系和社会的礼制,所以为过去的时代最为注重。
就夫妇、父子这两类基本的人伦关系来说,按《序卦》之序以及阐发同一思想的《荀子·大略篇》的讲法,夫妇乃是父子、君臣之本,比父子关系更为根本,这在一般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从古代社会的实际来说,夫妇关系之本“本”在繁衍出父子君臣关系,即它是为建构上下尊卑的父子关系服务的。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与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是问题的真正落脚点。
近年来新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载有《六德》一篇,讲述了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的“六德”。这“六德”尽管在文字表述上与“五伦”、“五常”有异,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即都在将家庭与社会视为一体的前提下,强调社会国家层面的道德需要。故父子、夫妇、君臣之间,是以先后、上下的关系来构建的。他们间最恰当的耦合,就是“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同上),从而使父子、夫妇、君臣各安其位、各循其职,天下也就由此而安定太平。
本来,自孔子以“爱人”作为其人伦关系的基础以来,“二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应当是家庭伦理的最核心的内容。但是,无论是看孟子的“五伦”、还是竹简的“六德”,“爱”在这里已经从无形中消失了,“伦”与“德”似乎都不再需要与“爱”相伴。夫妇之间,强调的只是各自的分位差别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主从关系。不过,在汉以前,儒家虽然在最高规范的层面已讳言夫妻有爱,但毕竟还有“夫妇”这一“伦”,夫妻关系有着不低于父子、君臣关系的地位而值得家庭和社会认真梳理,《序卦》和荀子还为此给予了特别的发明。但是,到了唐孔颖达疏解《尚书》“五常”的时候,则不但没有夫妻恩爱可言,连夫妇关系之“伦”也被取消了。
为什么?答案可能有多种,但关键之处其实亦不难设想,那就是淡化夫妇为的是强化父子,因为夫妇无论怎样“别”,它也是平行的关系,而封建国家需要的是上下的关系。只有上下即父子或父母子女的关系才能提供“孝”的准则,也才能由“孝”而推导和引申出封建时代最根本、也最为需要的维持上下尊卑关系的“忠”的原则。当然,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三纲”没有忘记妻,专有“夫为妻纲”一项。但夫既已为“纲”,那他与作为“目”之妻的关系,也就如同父子、君臣一样,成为了上下之间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了。
正是基于这一根本原则,旧时夫妻关系的必要性,其实就不在于夫妻本身,而在于父母子女的传承和孝道的延续。在日常生活角色中,家庭成员之间,由于女性的作用限制于生养子女,而不是参与社会国家的活动,所以,从家庭伦理到社会国家伦理的推广,主要地也就在父子而非母子一系。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母子之间相依为命,矛盾冲突较少也容易化解;而父子之间,由于同时连通着上下等级的利害关系,故矛盾也远较母子间为大。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在不同历史时代中,违背孝的原则而父子反目、亲子弑父者并不鲜见,然弑母者却几乎没有。这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对父子与君臣上下关系的互通性的举证。
从家庭关系自身来说,家庭的职能包括满足夫妻自身生活的需要、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需要、抚养和赡养的需要等多个方面。但由于这些活动都不可能脱离开社会来进行,所以,所谓家庭伦理,事实上都是以社会需要及评价标准为尺度,对家庭成员为满足其需要而进行的各项活动进行合理的规范和调节。在这里,家庭各项需要间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生育和抚养子女可以说是家庭最基本的职能和需要。正是因为如此,规范父子与夫妻关系的最终结果,便是父子有亲而夫妻不爱。
当然,说夫妻不爱并非就意味着它为家庭和社会所提倡。事实上,在“夫妇有别”之下的具体生活规范中,爱的成分是不难发现的,但是,在社会国家层面、在最高规范的立场上,夫妻的情爱则不能得到支持和提倡。爱在这里是限制于“别”、“随”、“和”等规范框架内而不能任意发挥的,它的目的亦在于为传承以“孝”为中心的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服务。也正是因为如此,社会国家往往是动员了一切的力量,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孝道的维护、传播和推广。
从而,在通过生育和抚养职能的实施而一代代传延的夫妻规范中,近代以来通常遭到人们非议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家庭伦理原则,其实并无可指责。孟子已将道理说得很明白:无后就意味着无孝。如果说,不同伦理原则和规范大多具有相对性的话,这一条却具有绝对的意义。“无后”即否定了种的延序,否定了种的延序,也就从物质基础上根本消解了孝之存在的可能。而一旦消解了孝,也就消解了儒家的整个仁义道德规范,消解了封建国家最根本的内在凝聚力。
(三)循礼与从上
从社会政治层面看,对于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他要处理的最根本的问题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民族关系上的天下一统,一个就是社会(阶级)关系上的国家稳定。由于天下一统自秦开始已经在总体上实现,故国家稳定的问题实际上成为了汉以后历代统治者的第一要务。从社会国家运转的实践来说,维持稳定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君臣上下关系代换成父子关系,以父之地位和孝的原则来化解社会国家的矛盾。《尚书·洪范》曰:“天子做民父母,以为天下主。”汉宣帝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书·宣帝纪》)正是因为看到了孝对社会国家稳定的巨大作用,所以汉家皇帝的谥号自汉惠帝以下皆称“孝”。同样因为如此,儒家十三经中,专门有《孝经》一部,它所讲述的道理,既是家庭伦理的纲领,也是社会国家伦理的大法。
“孝”既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孝呢?孔子对于“孝”有多方面的发明,但基本点是父母活着时给予物资和精神、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关照;去世后给予厚葬和适时的祭奠等。然而,子孙是否履行了孝道,其衡量的标准则在于礼即社会国家的规范。即便是家庭内部的孝顺与否,都是要用社会通行的礼义标准来维护和保障的。例如,曾子在孔门是以孝著称的,相传《孝经》便是孔子为他陈述而作。可曾子之孝,不仅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成分,更有不能违背国家礼制的成分。
在曾子临终前,身下铺着 国 君所赐的大夫才能用的席子,守候在身边的亲属、弟子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可服侍的童子却觉得有问题,并不顾他人反对,提醒曾子这不合礼义。曾子听后顿觉不安,坚持要其子女和弟子“易箦”(替换席子),并认为自己的弟子和孩子们对自己的爱(孝)不如童子。因为爱人、尽孝首先必须合礼,曾子不是大夫,他不应枕着大夫才能享用的席子辞世。人从生到死,不能于礼有违,心有不安,必“得正而毙焉,斯已矣”(《礼记·檀公上》)。曾子在他的最后时刻坚持“易箦,虽说是“反(返)席未安而没”,但他却可以放心无悔而去。直到他的生命的终了,也没有因为违背礼法而留下遗憾。在这里,礼法的价值要高于生命,死生之变不能动摇社会政治的根基。一句话,名分是绝对不能僭越的。这可以说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最根本的理念。
正因为如此,孝道所处理的就不止是直系血亲之间的家庭伦理关系,而且必然要映射到社会国家,调节整个的政治伦理关系。所以说,居处不庄重,不能叫做孝;事君不忠诚,不能叫做孝;居官不谨慎,不能叫做孝;交友无信用,不能叫做孝;征战不勇敢,不能叫做孝。何以这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都跟孝挂上了钩呢?那是因为这“五行”有了欠缺,必然会带来灾祸而殃及父母,所以人只有在任何社会活动中都做到了恭敬谨慎才能是孝(见《礼记·祭义》)。在已佚的《商书》中,不孝是被列为所有罪行中最重之罪去惩治的。而从正面来看,汉以后的官吏的选拔,通常都有“孝廉”的一科,孝行端正可以直接获官受职。作为中国职官制度的一大特色,它鲜明地突出了“孝”在社会国家政治伦理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从今天的立场来说,孝的绝对原则无疑具有许多负面的价值,最主要者就是孝所要求的下对上、幼对长的绝对服从乃至逆来顺受,张载的“存顺没宁”就是典型的代表:“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张载在本体论上虽主张“大心”,在伦理观上却倡导“小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西铭》)在这里,个人作为天地父母的所产,应当明白自己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做到知天、事天而养性。由于自孟子以来,心、性、天的范畴已在内在层面合而为一,故人对自我本性的保养,就是不懈地事天的过程。天地父母也就不只是外在之气,亦是内在之性,对父母尽孝就既需要保全自己的身体,也需要保养自己的本性。前者的榜样无疑是曾子,因为他能够全生以归而不辱父母;在后者,则大禹做得最好,他不喜欢逸情荡志的美酒而善于保养真性。
但是,如果仅仅止步于此,张载与前人的观点还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大禹、曾子的为孝而重生,乃是传统哲学已有的思想,张载的特点,是特别强化了为孝而受辱伤生、乃至弃生的原则。譬如张载所举的三个典型:舜帝是忍辱尽孝而最终使父母得到欢乐的典范;晋国世子申生为了不违父命,不得不自尽弃生;周大夫尹吉甫的儿子伯奇为尽孝,不得不顺从父意而甘愿被放逐。
申生和伯奇的例子在今人看来本是人间的悲剧,但在张载眼中却成当作了正面的典型来树立。他的道理在于,“我”个人只是天地间一藐小物,既然由天地父母所生,我的生命的价值及其一切活动,就当以反映天地父母的意志为指南,即应该以无条件的孝心来面对世间一切幸与不幸的遭遇:如果我有幸得到的是富贵和福泽,那是天地父母对我生命的厚待;如果我不幸得到了贫贱和忧愁,那也是天地父母用来锻炼我、以使我成就的手段。
就此不幸的待遇来说,或许可以看作为孟子当年思想的某种深化。孟子曾经说过,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赋予某人的话,那一定要以各种各样的与他本性相违的磨难来锻炼他,如使他的心意苦恼、筋骨劳累、肠胃饥饿、身体贫乏,这样才能培养出他坚强的性格和优异的才能。但是,孟子和张载,立足点是根本不同的。孟子的锻炼只是手段,动机和目的都是肩负大命而增益才能;张载的锻炼则要更为消极,它实际上已变成为目的本身,人所能做的已不比逆来顺受更多一点什么。而有幸的待遇,也成为了一种奢望,对于平民百姓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其实际的意义恐怕只剩下了那不幸的遭遇。
从此出发,世间的一切不公正也都变成了公正,人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天地父母对自己如此的“厚待”。必然的结果,就只能是:活着,我顺从世间的一切;死了,我宁静悄然地离去。如此“存顺没宁”的意义,在于说明现存的社会秩序天然合理,从而使心灵从人生的悲欢离合中得到最根本的解脱,泰然面对一切生死离别及各种人间的苦难。但由此一来,张载看重的,也就不是人的现实生命,而是以生命和生存权的放弃为代价的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宗教式的临终关怀了。
(四)至善与事功
从“存顺没宁”出发,对于一切生活于社会大家庭中的“我”来说,尽孝与尽忠实际上是一体不二的,不忠不孝之人自然就当受到最彻底的否定。但是,忠与孝相较,践行孝道毕竟有自然血亲的先天根据,履行忠的义务却完全依赖于主体的道德自律,故有时也并不那么确定。比方,作为忠之对象的“国”与“君”之间,通常是一体不分的,但历史也会出现二者分离的情形,这时对尽忠之人来讲,就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宋初的张载显然还未遇到如此棘手的问题,但对生活于宋末的文天祥来说,他虽然谨守“为臣止忠,为子止孝”的忠孝不二原则,但却必须对“忠”进行限定,最后做出了弃君而守国的选择。一句话,君必须与国联系在一起,忠君才可能具有正面的价值,才可能与“止于至善”相联系。
因为,无论是止于忠还是止于孝,中心都是止于至善,这也是“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人才培养的最终指向。所以孔子强调要“知其所止”。在这里,至善或忠孝不二的原则所以能成为所当“止”之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家庭伦理和社会国家伦理结合的最高典范。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也。如此以上下关联为前提的孝道模型,同样是以互相爱慕为基础的夫妻情爱的牺牲为代价的。但《大学》如此讲,有它自己的理由,即作为治学为道的目的的“盛德至善”之功本已超越了家庭,终使天下百姓普受其恩惠,事功已经成为孝道的组成部分。
作为儒家的经典,从《大学》到《中庸》,“孝”的理路是一贯的。上下的交通要远重于左右的和谐,漠视的仍然是夫妻的情爱。在这里,家族的延续和事业的拓展,通过父子、祖孙的前后继承关系具体彰显了出来。《中庸》赞许武王和周公的“达孝”,而其内容,则在他二人对各自祖先的事业的继承。“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中庸》)。即武王继承了太王、王季、文王之绪而发扬光大,终至占有天下;周公则完成了文王、武王的德行和事业,追尊先王,安定了周的统治和基业。如此的“继志述事”之孝,当然首先是社会国家伦理,但毫无疑义,它也同时就是周王的家庭伦理。
《孝经》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为孝之始,而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为孝之终。又说:“夫孝,始于事亲,中 于事 君,终于立身。”事功和成就的方面在这里得到了特别的推崇。可以说,这也是孝道留给家庭和社会的最可宝贵的精神。孝在行中,在创造而不在守成,只知守孝而事业无成,父母不快,门楣无光,才是最大的不孝。立身行道对孝的推广,实际的意义正在于以社会伦理引导家庭伦理,使家庭伦理落实于社会伦理。在这里,光宗耀祖的孝道观念本身与懒惰和不履行为父、为子的职责的行为是不相容的。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激励着士子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
(五)夫妻爱与男女通
公元19世纪末,维新派的杰出代表谭嗣同在他的主要著作《仁学》中,从平等致一的“通”的原则出发,对先秦以来以“五伦”为代表的仁爱原则重新进行了梳理。他认为,五伦中的前四伦形式上是以亲、义、别、序为各自谨守的原则的,但由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这四组“二人”之间已经处于不同的地位,已是具有不同分位、差别之人,故所谓亲、义、别、序,实际上都成为了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别原则的具体落实。只有朋友一伦可以说是例外。因为“朋友”的概念本来只有在以诚信为基础的平等交往中才可能成立。故凡为朋友,个人均具有“自主之权”,而可以不考虑各自不同的地位、身份问题。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上下通、男女内外通的目的,真正将仁爱落到实处。
谭嗣同的观点的进一步引申,就是父子、夫妇、长幼之间都可以做朋友,可以以朋友一伦去改造其它四伦,使各伦之间都以“爱”来贯穿,既循原始儒家仁爱之本意,同时也添加进了现代民主、平等的新的内容。但鉴于父子、长幼之爱本来有着基于血缘亲情的天性,故最需要提倡和打“通”者,乃是传统社会最受到压抑的夫妻情爱。夫妻之间、男女内外,其规范由“别”而到“通”,虽然跨出的是巨大的一步,嫁接的是西方文化的精神,但它却不会因之而抛弃丰厚的传统思想资源,所以谭嗣同以为“多取义于《易》,以阳下阴吉,阴下阳吝,泰否之类故也”(《仁学·仁学界说》)。在这里,阴先于阳,并非又倒转为阴主阳从,而是更为充分地发挥了各自的品性,实现了双方的亲和交感,体现的是平等相爱的精神。这虽为后儒所不愿言,但却为家庭和社会所必需。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02年第1期。